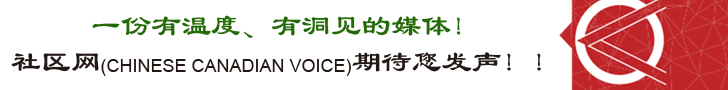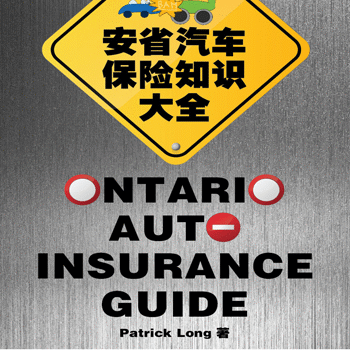
白宫发言人Karoline Leavitt(卡洛琳·莱维特)关于对加拿大关税”无豁免(No exemptions)”的声明,标志着特朗普(Donald Trump)政府贸易政策进入新的激进阶段。这项以”互惠关税(Reciprocal tariffs)”为名、实则带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,不仅将重塑北美经济一体化格局,更暴露出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的重大转向。
法律工具的政治化运用具有典型特征。特朗普借助《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》(Inter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Powers Act,简称IEEPA)将北部边境宣布为”紧急状态”,此举遭到民主党参议员Tim Kaine(蒂姆·凯恩)的强烈质疑。从政策分析角度看,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张存在三重争议:一是将禁毒议题与全面关税捆绑缺乏数据支撑(边境芬太尼截获量微不足道);二是绕过国会正常审议程序;三是为富人减税提供资金来源的嫌疑。这种”政策工具创新”实质上削弱了美国贸易决策的制度约束。
“对等关税”的理论缺陷在实施层面显露无遗。特朗普所谓的”解放日(Liberation Day)”关税逻辑存在根本性矛盾: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,其关税承受能力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根本不对称;将汽车关税与北美自贸协定(Canada-U.S.-Mexico Agreemen,简称USMCA)原产地规则挂钩的操作,更会造成”双重征税”的荒诞局面。值得注意的是,政府内部对具体执行标准仍存在明显分歧,这种决策混乱已经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波动(标普500指数下跌0.4%,纳斯达克下跌1.2%)。
该政策对北美产业链的破坏性影响正在显现。加拿大作为美国最大能源供应国(2021年占美原油进口量51%),其石油行业已遭受10%的针对性关税打击。若叠加即将恢复的全面关税,汽车制造业等跨境产业链将面临50%的复合税率。安大略省长Doug Ford(道格·福特)与美商务部长沟通无果的案例表明,加方在政策预期管理上已陷入被动。
值得玩味的是政治周期与贸易政策的互动。特朗普在4月28日加拿大大选前突然软化态度,与特鲁多继任者Mark Carney(马克·卡尼)进行”非常良好”的通话,这种战术性缓和暴露出其关税政策的非经济动机。但周日”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”的言论又重现了经济民粹主义的本质,这种矛盾姿态可能意在影响加拿大选举政治。
从更广视角看,这场关税危机揭示了美国战略文化的深层变革。将北约盟友加拿大贬为”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”,不仅违背了七国集团的基本外交准则,更标志着”自由国际秩序”理念在华盛顿的式微。当白宫将贸易逆差简单等同于”吃亏”,实际上否定了战后美国自己主导建立的全球分工体系。
当前局势发展存在三种可能路径:若民主党成功推动IEEPA表决,将迫使共和党人在”忠诚特朗普”与”维护宪政”间公开站队;加拿大可能通过WTO争端机制结合跨党派游说来延缓措施;最危险的可能是加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,使北美自贸区陷入”以邻为壑”的恶性循环。无论哪种情况,特朗普政府这种打破禁忌的贸易举措,正在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树立危险先例。